《第八個嫌疑人》:過于真實的無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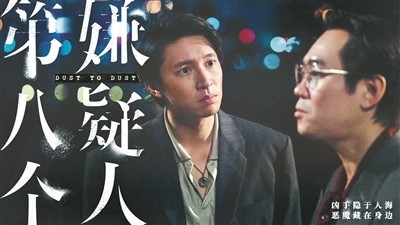
◎任凡
盡管片名起得非常懸疑,電影《第八個嫌疑人》卻完全不屬于懸疑或心理驚悚的類型,想看燒腦推理或反轉的觀眾可以放心繞行。大部分00后觀眾對該片的操作手法或許會感到相當陌生:既沒有類型片里常見的追車槍戰,也沒有絲絲入扣的分析推理,有的只是粗糲的場景再現和毫無閃躲的全知視角。那么,它到底拍了個啥?
真實案件改編的潮起潮落
雖然按照當下的電影分類標準審視,該片很難被歸類,但這種基于真實案件改編而來的影片或劇集卻曾在世紀之交風靡一時。其中較為出色的如《征服》《12·1槍殺大案》上映時,說萬人空巷似乎也不為過。至今這些影片在豆瓣網的評分仍然高到令人咋舌。
彼時,中國大陸電影工業尚不成熟,類型化剛剛起步。什么人物弧光、敘事節拍、三幕劇作法,統統不重要。只要畫面看著像真的,觀眾就很買賬。于是,海量真實案件就為這種樸素的市場需求提供了極大的滿足。比如,《12·1槍殺大案》甚至請來了參與破案的干警自己演自己,收獲的效果相當不錯。隨著影視劇作品市場化進程的加快,觀眾欣賞水平逐步提高,再加上審查等場外因素,真實案件改編類作品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偶有這類訴求的創作者也會盡量找出一個類型賣點植入影片中,比如《解救吾先生》里階層差異制造的人物心理變化,以及《除暴》里的格斗爽片路線。
《第八個嫌疑人》拍攝于2019年,那時張頌文還沒有爆火,大鵬還在嘗試轉型,可影片卻時至今日才得以上映,這類作品登臺亮相的難度可想而知。雖然片尾掩耳盜鈴一般打出了“本片純屬虛構”的字眼,觀眾還是不難發現它是自1995年廣東番禺運鈔車搶劫案脫胎而來。雖然全部使用了化名,但片中的時間跨度、案件經過和犯罪分子構成,幾乎和原案一模一樣。
如前文所述,高度寫實放在20年前毫無疑問是個優點,可時過境遷,面對如今的觀眾卻未必能過關。在當下的審美語境里,真實只是一個方面(甚至不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除此之外,觀眾需要更加豐富的戲劇沖突和人物關系變化,以及潛藏于文本之下的社會向表達。可以想象,在四年時間里,主創們經歷了怎樣艱辛的修改,終究敵不過諸多掣肘,最終制造出一種過于真實的無聊。
語焉不詳的模糊表達
陳信文怎么就從一個生活富裕的建筑公司老板變成了鋌而走險的搶劫犯,王守月又是為什么執意要在從警察局退休前單槍匹馬地千里追兇?這些蘊含的豐富心理層次和行為動機都被簡單地一筆帶過,而邪不壓正的結果就像預先寫好的程序一樣跟在回車鍵后面自說自話。不客氣地說,這樣簡單粗暴的劇本操作,其過時程度和片中出現的BP機相差無幾。
既然在戲劇邏輯和人物塑造上都不占優勢,就只好在場面上營造張力。警匪時隔多年后重逢的那場餐桌戲處理得的確不錯,換了身份的陳信文在明知被識破后怎樣與王守月虛與委蛇,是全片為數不多的看點。然而,片段再精彩也終究是片段,還是無法抵消通篇敘事的乏力與乏味。此外,為了增強人物色彩,片中還刻意植入了一段陳信文兄弟少年時打劫出租車的前史。但這究竟是要說明犯罪基因早早種下,還是企圖闡釋“勿以惡小而為之”的勸誡,都通通湮沒在一片語焉不詳的模糊表達里。
小角色的定位與演繹
還想說一說角色與演員的問題。“只有小演員,沒有小角色”這句聽爛了的勵志雞湯似乎很有道理,細想之下其實全無營養。小角色就是小角色,有什么不好意思面對的呢?的確,角色的大小不在于戲份多少,可跟演員的表演也沒特別大的關系,全在于劇本給予角色的支撐和該角色在全劇中發揮的作用。就像《茶館》里的松二爺只有區區一場戲,可誰演誰出彩,這就不是小角色。相反,滿場飛奔的王大栓喊得再賣力氣也沒法兒讓人記住他,誰演也不行,這就是小角色。
由是觀之,該片中的何藍就是個小角色,其工具人屬性毫無爭議。張頌文演技再炸裂也像武林高手一拳打在棉花上,根本沒有施展余地。而引來贊譽的大鵬所謂的“突破性表演”,不過是因為陳信文逃亡后活在莫志強身份里的角色設定,給予了演員足夠的發揮空間。如此想來,張頌文如今的爆紅決不是由于他認真演了幾十年小角色而最終修成正果,完全是因為他等來了“高啟強”這個大角色。
縱觀全片,或許有一個細節值得玩味。陳信文承包的修橋工程遲遲無法動工,他對外給出的解釋是地質結構存在問題,因此耗費了大量資金。這時一位領導模樣的人搖下車窗警告他不要亂講話,隨后揚長而去。由此,陳信文才選擇了鋌而走險,最終走上了惶惶不可終日的犯罪之路。
陳信文犯罪的動因無疑是該片的原初驅動力,到底是他揮霍成性造成了資金缺口還是其他什么不可言說的原因?反觀片名《第八個嫌疑人》,表面上是七名犯罪分子加上一個改頭換面逃亡多年的莫志強,可情況真如“7+1”這么簡單嗎?七名罪犯無疑是法律層面的罪魁禍首,可躲在暗處那第八個嫌疑人恐怕才是造成一連串慘劇的幕后元兇。那么,他又到底是誰呢?
隨便看看:
相關推薦:
網友評論:
推薦使用友言、多說、暢言(需備案后使用)等社會化評論插件






